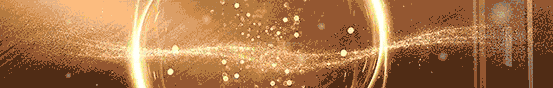城市收縮”與“城市擴張”兩股力量針鋒相對,但同時存在,誰也不會真正消滅對方,正如電梯和地鐵可以并存,這個世界不是非此即彼的,它是對立統一的,是求同存異的。
我們可以把這兩股力量的交鋒,闡述為電梯與汽車的競賽,現在汽車又多了一個友軍,那就是地鐵,而且比汽車更強大。
地鐵跟著地鐵買房,還是跟著電梯買房,這是一個問題。
電梯是向上要空間,代表著城市的收縮趨勢,象征著城市的密度。汽車與地鐵則向遠方要空間,代表著城市的擴張趨勢,象征著城市的廣度。
電梯如果打敗地鐵,城市收縮會占據主導優勢。地鐵如果打敗電梯,城市擴張會占據主導優勢。二者的勝負直接決定了你資產配置的邏輯:跟著地鐵買房,還是跟著電梯買房,這是一個問題。
這場“戰爭”曠日持久、歷久彌新,在西方國家已經打了幾百年,目前勝負未分。
以現代城市文明的高地——美國為例。誕生最早的那些城市,比如紐約和芝加哥,都是高密度城市的杰作,到20世紀上半葉,紐約與芝加哥瘋狂地向上生長,1931年就能建造出381米高的帝國大廈,電梯成為這些城市的力量支柱與精神象征。
但福特汽車的一聲炮響,讓汽車進入了尋常百姓家,人們日常的出行半徑實現了至少十倍的飛躍,城市因循千年的古老邏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:在汽車時代,聚集還有必要嗎?密度還有必要嗎?
密度原本不是城市的驕傲,而是城市的無奈,受限于交通工具的落后,人們的社會經濟活動半徑只能限定在一個很小的范圍內,否則城市無法高效運轉。馬車時代,這個“很小的范圍”也許只是一個半徑為5公里的圓,但它就是城市尺度的天花板。
高密度城市帶來了擁擠、環境污染、傳染病等各種社會問題。例如,十九世紀末的倫敦,由于工廠的聚集和工人居住區擁擠無序的建設,造成了霍亂等傳染病的擴散,這些因密度而付出的代價,讓人們開始懷疑城市的價值。
所以,當汽車普及之后,人們赫然發現,職住是有條件分離的,居住在農村、工作在城市成為一種理想生活的倡導——這樣既能享受到城市豐富的經濟社會資源,又能享受到田園生活的低密度與大空間。
理論家開始為此搖旗吶喊,英國社會活動家霍華德恰到好處地提出了“田園城市”理論,他在著作《明日,一條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》中認為應該建設一種兼有城市和鄉村優點的理想城市——“田園城市”。田園城市實質上就是城市和農村的結合體。
1933年,法國建筑大師勒·柯布西埃在雅典召集全球規劃師,簽訂了后來被規劃行業奉為圭臬的《雅典憲章》。針對當時工業化、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嚴重傳染病和環境污染,這個文件提出了“功能分區”的重要理念。功能分區的外在體現就是“職住分離”和“降低密度”,它和霍華德的“田園城市”前后呼應。
田園城市主義與雅典憲章精神很快成為城市規劃的主流理論,并深刻地影響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城市的發展。今天你走進全世界大部分恢宏的城市,幾乎都能在里面找到雅典憲章的痕跡。
主流規劃理論直接導致了美國城市中心區的空心化(也稱逆城市化),直到今天,你走進美國中西部的一些大城市,仍能感受到一種與中國城市完全不同的現象,那就是白天熙熙攘攘的市中心,一到晚上就讓人避之不及,因為代表城市文明的中產階級都已回到郊區的住所了,只有各種危險的流動人口仍然活躍在市中心,而市里的那些高密度公寓也基本住著窮人。在這些城市,電梯與汽車并存,相得益彰。
而在美國的西部,很多城市把這個理論貫徹走得更徹底,比如洛杉磯、菲尼克斯、休斯頓等城市幾乎完全拋棄了密度,它們“大馬路+獨幢住宅+花園”的擴張模式,使整個城市如同郊區,以致沒有一個明確的市中心概念。在這些城市,汽車則完全打敗了電梯,后者幾乎沒有存在的必要。
電梯電梯是向上要空間,代表著城市的收縮趨勢,象征著城市的密度。
在主流規劃理論統治世界城市半個多世紀之后,這套理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評,以彼得·卡爾索普、簡·雅各布斯為代表的西方學者厭惡郊區,他們認為主流規劃理論導致城市的無序蔓延、高能耗、多樣性丟失等問題,他們開始向古典城市致敬,希望城市把擴張的觸角收縮回去,倡導人們回到中心區去,歷史又回到了一百年前嗎?
于是,針對主流規劃理論的新城市主義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走紅,原本被奉為經典的那些田園城市,比如洛杉磯、休斯頓成為理論抨擊的“負面典型”。今天的美國城市,重振中心區成為一種政治正確。
你看,電梯與汽車的力量格局又發生了變化,電梯沒有被真正打倒,它正在卷土重來,試圖與汽車、地鐵重新爭奪城市的統治權。
站在一個長的時間緯度,城市發展可謂“密久必松、松久必密”,電梯與地鐵的競賽其實沒有輸贏,城市的歷史更像是循環往復的游戲。
今天的中國,地鐵與電梯,城市擴張與城市收縮,代表著城市發展的兩股力量,它們正在發生一場前所未有的競賽,誰勝誰負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得知道你的城市正處在哪個發展階段,是田園城市外向擴張的階段,還是新城市主義內向收縮的階段?這個決定了你當下的資產配置邏輯。

上一篇:電梯壞了一周沒修好